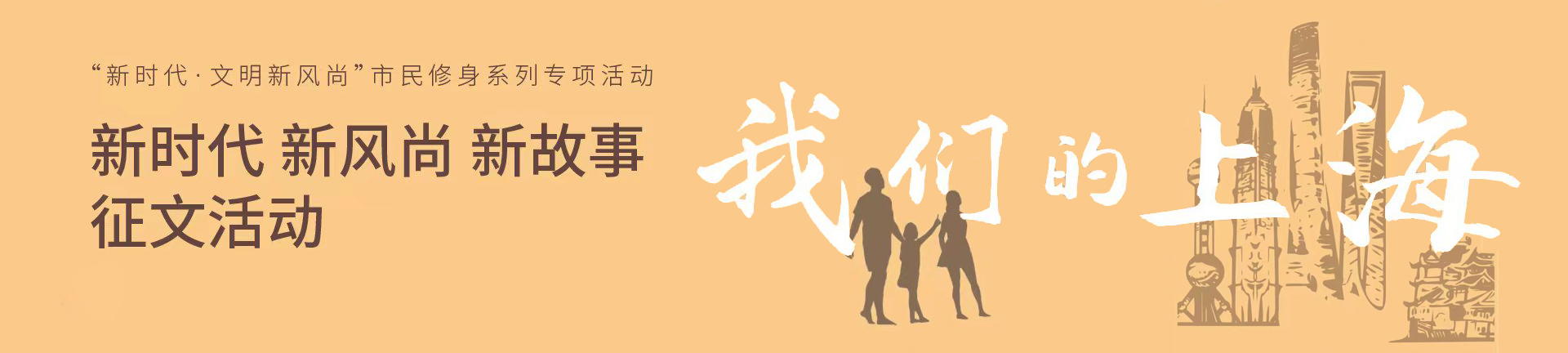
在众人关切的目光中,一位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稳步爬上扶梯,登上了不满周岁的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深潜器。在南海的万顷波涛中,“深海勇士”号缓缓驶向海底的沉积珊瑚礁,观察采样长逾8小时。
这位耄耋老人,就是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的汪品先教授,一位82岁高龄、依然拥有一颗“赤子之心”的科学大家。
谈及自己在众人眼中的深潜壮举,汪品先说:“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。”
2017年,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制的“深海勇士”号4500米载人深潜器成功海试,2018年投入实验性应用。汪品先第一时间决定使用“深海勇士”号及其科考母船“探索一号”,执行他领导的“南海深部计划”西沙深潜航次任务。
汪品先说:“作为一名海洋科学家,到海上观察研究大海是很平常的事。我期待有更多的海洋科学家走出实验室,到大海中来。海洋知识的根源在海洋,海洋科学的灵感在海洋。在大楼里写论文固然重要,但是科学家不能专靠学生出海取样。”
现代科学的发展,原本就源于人类的好奇心。从小,汪品先就喜欢遐想。他曾在《院士自述》里写道:“独坐静思,其实是十分有趣且有益的。我喜欢在飞机上观赏云海变幻,真想步出机舱在白花花的云毯上漫步;也喜欢在大雨声中凝视窗外,想象自己栖身水晶宫的一隅……”
在6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,这种好奇心不断引领着汪品先,一步步深入探索海洋与地球科学的前沿奥秘。
从第一次以中国的首席科学家身份主持设计20年前的国际大洋钻探航次,到推动我国大洋钻探“三步走”;从推动并主持我国“南海深部计划”,到建造我国海底观测网……他的每一次好奇,都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。
20多年来,这是汪品先第四次南海科考航次,进行国际前沿研究。前三次他都乘坐外国的船,这次却是乘坐我国自己的船、自主研制的载人深潜器,亲眼去观察南海的海底。汪品先说:“这趟海底的旅程,真像爱丽丝漫游仙境,我刚从仙境回来。”
在“探索一号”科考船上,这位82岁的科学大家,每天都会参加科考讨论会,发表自己的看法,认真倾听小辈们的意见,与大家一起规划考察路线,并根据实际情形,实时修改原先计划,谦逊而随和。
但在生活上,他却像孩子一样固执,拒绝了船上所有的特殊待遇。一日三餐,他像所有的考察队员一样,在船上爬上爬下;在风浪的颠簸中,他依然坐在电脑前工作,就像在陆地上一样,惜时如金。
汪品先还像孩子一样,毫不忌讳地谈论着健康与生死。船医给他量血压,他得意地说:“看,我的血压像小伙子一样棒,不过是靠药物控制的。”2017年底,他被查出了前列腺癌,医生的保守治疗方法,帮他控制了病变指标。这次上船,他仅带了一支皮下注射的针剂。
“到了我们这把年龄,都是排着队等着‘走’的,有的人还要来插队。”汪品先幽默地说,“别人是博士后,我是做院士后。我国的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以来最好的时机,许多我年轻时想做而做不成的事,到了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,怎能不抓紧宝贵的时间?”
“其实作为海洋地质工作者,我出海的机会并不多,并不是因为不愿意出去,而是出去一趟取回的样品可以做好多年。1999年大洋钻探航次的样品现在还在分析。”汪品先强调,自己并不认为海洋科技工作者必须不断出海,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许多同行不愿意出海。
说着,汪品先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。
当时一位美国海洋地质学权威学者来到我国。汪品先向他当面请教:如果你是中国人,能做什么方面的研究?
对方想了想,回答:考证中国古文献潮汐信息。
汪品先理解,那时我国海洋科研硬件条件差,船也少,相比起来,只有古文献才是优势。而如今,我国海洋科研硬件提升了,却缺乏了一种科学精神。
“不仅是海洋领域的科学家,包括自然科学家,大家面向自然的兴趣和勇气在下降,都喜欢在大楼里面对着计算机,习惯了穿着白大褂的实验室。”在汪品先看来,有人行政事务繁忙可以理解,但作为一个群体,学科带头人长期脱离现场,相当于切断了探索自然的“源头”。
这些年,汪品先在多个场合一直重复这样一句话:“我们不能只做‘外包工’。”从外国文献里找题目申请立项;买外国的仪器做分析;再到外国发表文章——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学创新的要害。
“要改变这种现状,必须从‘源头’抓起。”汪品先认为,好奇心应该是科研人员提升面向自然的兴趣和勇气的最大驱动力,“如果你的职业就是你的爱好,这最好。真的科学家不一定要去想为了什么,只是因为喜欢。我的研究有用,那太好了;即便没有用,我还是要研究。”
没登过阿尔卑斯山,就难以理解山脉的复杂构造;不下潜,就对海底缺乏感性认识。汪品先下潜三次,也是身体力行地想鼓励年轻的科研人员到一线去,只坐在实验室里写写论文,做不出好的研究,也不是真正的创新。
“一个人一生经历的幅度,才是这个人的价值。否则一根直线平平的,太没意思了。”用这句话来概括汪品先这位“深海勇士”,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供稿: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文明办
作者:聂阳阳